常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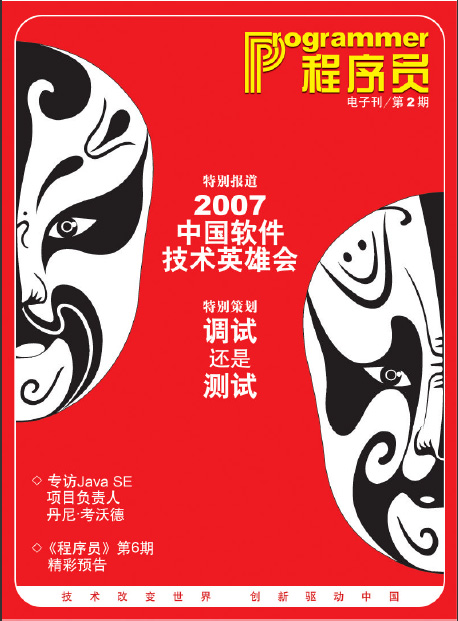
《程序员》杂志封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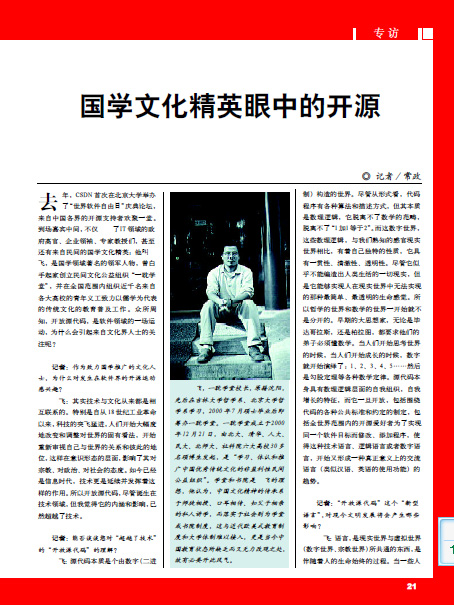
文章版面图影
去年,CSDN 首次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世界软件自由日”庆典论坛,来自中国各界的开源支持者欢聚一堂。到场嘉宾中间,不仅荟萃了IT 领域的政府高官、企业领袖、专家教授们,甚至还有来自民间的国学文化精英:他叫逄飞,是国学领域著名的领军人物,曾白手起家创立民间文化公益组织“一耽学堂”,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近千名来自各大高校的青年义工致力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普及工作。众所周知,开放源代码,是软件领域的一场运动,为什么会引起来自文化界人士的关注呢?
记者:作为致力国学推广的文化人士,为什么对发生在软件界的开源运动感兴趣?
逄飞:其实技术与文化从来都是相互联系的。特别是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的突飞猛进,人们开始大幅度地改变和调整对世界的固有看法,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和彼此的地位,这样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影响了其对宗教、对政治、对社会的态度。如今已经是信息时代,技术更是延续并发挥着这样的作用。所以开放源代码,尽管诞生在技术领域,但我觉得它的内涵和影响,已然超越了技术。
记者:能否谈谈您对“超越了技术”的“开放源代码”的理解?
逄飞:源代码本质是个由数字(二进制)构造的世界。尽管从形式看,代码程序有各种算法和描述方式,但其本质是数理逻辑,它脱离不了数学的范畴,脱离不了“1加1等于2”。而这数字世界,这些数理逻辑,与我们熟知的感官现实世界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性质,它具有一贯性、清澈性、透明性。尽管它似乎不能编造出人类生活的一切现实,但是它能够实现人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那种最简单、最透明的生命感觉。所以哲学的世界和数学的世界一开始就不是分开的。早期的大思想家,无论是毕达哥拉斯,还是柏拉图,都要求他们的弟子必须懂数学。当人们开始思考世界的时候,当人们开始成长的时候,数字就开始演绎了:1、2 、3 、4 、5 ……然后是勾股定理等各种数学定律。源代码本身具有数理逻辑层面的自我组织,自我增长的特征,而它一旦开放,包括围绕代码的各种公共标准和约定的制定,包括全世界范围内的开源爱好者为了实现同一个软件目标而修改、添加程序,使得这种技术语言、逻辑语言或者数字语言,开始又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交流语言 (类似汉语、英语的使用功能)的趋势。
记者:“开放源代码”这个“新型语言”,对现今文明发展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逄飞:语言,是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数字世界、宗教世界)所共通的东西,是伴随着人的生命始终的过程。当一些人(如诗人),处于在这些不同世界交汇点的时刻,由于激昂的信力,语言符号会立刻空前丰富,他会随时出口成章作出诗歌来。现在人类的心灵,所面临各种困难和沉重,其实是由各种世界的不同语言彼此交融交汇时,产生冲突而引起的。所以现今文明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语言本身的多样性和语言秩序的混乱性所引起的。比如,目前世界上不同的民族,不仅存在不同的语言,而且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开放源代码后产生的新型数字语言,具有公共性,同样一个程序,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会有同样的理解。这就保证了不同文化之间,可以产生某种“通约”,这对各个民族语言文化的进一部互相理解会有帮助作用。总之,这样的数字语言,通过在网络平台下的开放,保证了自我组织和演绎性、集体参与性、公共性等特征,这对我们进一步思考在未来如何沟通各种文化、重建语言秩序,恢复各种思想本身具有的原始弹性,并将它们引入我们的常态生活,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记者:有人预言,未来只有推广体现“开放精神”的开源运动,才会带来一个“可知社会”,进而形成一个“可信社会”,您怎么看?
逄飞:这种思路如果作为一种概念提出来,在纯粹的数理逻辑世界是有效的,但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只能作为一种诉求,而不是固化的方法措施。而一旦成为“诉求”,这种逻辑的演绎,本身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人类世界。等于说人们由于对现实生活的不理解,而去假借逻辑的名义,创造了一个“非驴非马”的东西。人和人之间,不可能存在完全的“信”与“不信”;正如我们不可能脱光所有的衣服到大街上裸奔。有时候,不开放,同样是好事情。所以引申到软件领域,提倡开源,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反对所有“闭源”的商业软件。尽管当初StallMan 发动以开源为核心的自由软件运动时,一再强调这是“道德工程”,但人们更愿意从技术创新、商业利润的角度来评估它的价值。而近年它的蓬勃发展昭示,它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不少有远见的政界、文化界人士已纷纷开始从各种角度吸收其营养。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技术运动与政治文化运动从来都是密切相关;正如逄飞所言,“技术,它正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不仅可以唤醒文明历史初期、人类刚刚站立起来时候的源代码,甚至可以唤醒这几千年来整个人类灵魂当中所积累的源代码。”
逄飞,一耽学堂校长,原籍沈阳,先后在吉林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2000 年7 月硕士毕业后即筹办一耽学堂。一耽学堂成立于2000年12 月21 日,由北大、清华、人大、民大、北师大、社科院六大高校30多名硕博生发起,是“学习、体认和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非盈利性民间公益组织”。学堂和书院是逄飞的理想,他认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系于师徒相授、口耳相传、如父子相亲的私人讲学,而落实于社会则为学堂或书院制度,这与近代欧美式教育制度和大学体制难以接入,更是当今中国教育状态所缺乏而又无力改观之处,故有必要开此风气。